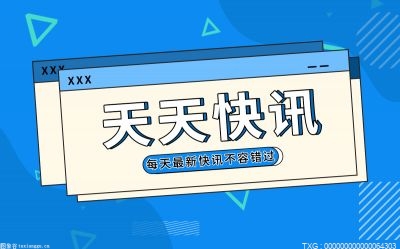作者:卞毓方
 【資料圖】
【資料圖】
人說“有其父,必有其子”,那么,父親身高一米八,我應該長到一米八五,甚至一米九,才對得起達爾文的進化論。遺憾啊遺憾,我最終僅躥到一米七三,其余二兄一弟,還不如我,兩個姐姐,更甭提了。
我為什么不能青出于藍,后來居上?家人一致認為,首先是先天不足。母親大人生得過于玲瓏,也就一米五出頭,正應了俗諺“爹矬矬一個,娘矬矬一窩”,我的一米七三已屬僥天之幸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其次是后天營養(yǎng)匱乏,正在高速成長的當口,碰上了三年困難時期,饑腸轆轆,果腹成了頭等難題,還長什么長。
父親有頂禮帽,深灰色的,冠高而圓,頂部呈三角形凹陷,底部系以黑色緞帶,帽檐寬大而略微翹起。聽母親講是早先闖蕩上海時置的,上海人講究“行頭”,出客必須穿戴入時。我懂事后,偶見父親戴過一次,是去興化出席二哥婚禮時。其余日子,禮帽一直放在紙盒里,紙盒擱在竹棚上。說不清從哪一天起,我萌生了一個大膽的宏愿:將來,這頂禮帽歸我。
將來是什么時候?喏,就是等我長得和父親一樣高時。小學期間,我曾無數(shù)次偷著試戴,那禮帽拿在手里,溫如玉,軟如絨,闊綽而又帥氣。“馬中赤兔,人中呂布”——呂布若生在今天,恐怕也要棄了紫金冠,改戴大禮帽吧,如此才前衛(wèi)、拉風。唉唉,可惜帽冠太大,我的腦瓜又太小,往頭上一套,帽檐一直滑溜到眼睛,禁不住想起成語“沐猴而冠”。沒關系,我還小,有的是長高長壯的機會。
到了高三,悲哉,我的身高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定格,再次試戴,仍然嫌大。散場敲鑼——沒戲了。從此只能仰望父親高大的背影興嘆,那頂禮帽或許在竹棚上竊笑,是的,它屬于魁梧,屬于偉岸。
小時候,沒人說我長得像父親。除了身高不及,臉型也不像,父親的臉明顯偏長,我的近似于圓;五官也不像,父親的線條是儒家的,外柔而內剛,我的線條卻是剛的,更準確地說,是粗糙的;脾性也不像,父親詼諧、幽默,我則木訥、無趣。
夏日晚間,一幫小孩捉迷藏,玩得興起,夜深了也不歸宿。這時,各家大人就會出來找。找著了,還賴著,不肯回,大人出手就打:“讓你瘋!讓你瘋!”父親也會出來找我,他號準我的脈,料定我會往哪兒躲,一下子就找個正著。見了面,老遠揚起右手,作狠抽狠揍狀。我曉得,那是唱戲的胡子——假生氣,父親的巴掌不會落下,嚇唬而已。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,也沒有打過弟弟。
父親在家里,從來不發(fā)脾氣;對外人,更是笑顏相對。四弟元氣足,瘋勁大,拳頭硬,諢名“四亂子”,與小朋友玩耍,常常話不投機就“看家伙”。那些吃了眼前虧的孩子哭哭啼啼回家找大人訴苦,有的家長就找上門來,向我父親告狀。父親總是千賠禮,萬道歉,答應等“四亂子”回來,好生收拾收拾。四弟察知有人告狀,躡手躡腳踅回,躲在屋角,等著挨訓。然而父親視若無睹,仿佛啥事也沒有發(fā)生。
是出爾反爾、自食其言嗎?非也。父親對鄰里關系是看得很重的,“行要好伴,住要好鄰”“惱個鄰居瞎只眼”是他的口頭禪。事后見了那曾被四弟欺負的小朋友,他總會摸摸頭,拍拍肩,好言撫慰。父親對四弟的“劣行”睜一只眼,閉一只眼,并非放任自流,而是“知子莫若父”,他曉得四弟只是頑童意氣,爭強好勝,骨子里還是個仁義的孩子,知羞恥,識好歹——父親有句掛在嘴邊的話:“牛大自耕田。”因此,對一時過錯無須責打,重在以身作則,言傳身教。果然,四弟上學后,各方面表現(xiàn)皆優(yōu)。
為人處世,父親常講,宰相肚里能撐船,小肚雞腸成不了大事。他跟我講過兩個故事,特別強調,是祖上傳下來的。
其一,“秦穆飲盜馬”。秦穆公丟了幾匹馬,派負責養(yǎng)馬的官員去找。官員回報:“馬兒已經被三百多個農夫殺了分吃,我把這幫不知好歹的家伙統(tǒng)統(tǒng)抓了來,國君您看如何處治!”秦穆公說:“別,別,哪兒能因為幾匹馬,就把這么多百姓都抓起來呢?我聽說馬肉不是尋常食物,吃它時必須喝點兒酒,否則會傷腸胃。趕緊給每人都喝點兒酒吧,然后放他們回家。”三年后,秦國與晉國爆發(fā)戰(zhàn)爭。秦穆公被圍,身負重傷。節(jié)骨眼上,那三百個農夫趕了來,舍命將秦穆公救出。
其二,“楚客報絕纓”。楚莊王打了勝仗,大宴群臣。由晝達夜,點燭狂歡,并令愛妃許姬給眾人敬酒。許姬來到某一桌時,恰值風吹燭滅,黑暗中有人趁機拽了一下她的衣袖。許姬不是好惹的,她把對方的帽纓扯斷,以此作為罪證,請求莊王查處。莊王焉能和妃子一般見識,他當機立斷,提高嗓音,宣布:“諸位都把帽纓摘下來,以盡今日之狂歡!”蠟燭重新點燃,因為大家都摘了帽纓,那個趁暗非禮的家伙得以逃過一劫。七年后,楚莊王率軍攻打鄭國,不料被鄭國的伏兵包圍,陷入絕境。千鈞一發(fā)之際,楚軍副將唐狡單槍匹馬沖入重圍,救出了莊王。事后,莊王重賞唐狡,唐狡辭謝,說:“那年,在宴席上對許姬非禮的,正是微臣,蒙主公不殺之恩,是以今日舍身相報。”莊王聽罷感慨萬千。
這兩個故事,令我想到祖父的待人接物,原來這是“家學”。
竹棚上,在禮帽盒的旁邊,還擱著一根扁擔。這也是文物級的古董,串聯(lián)著父親前半生的許多故事。父親說,這扁擔是曾祖父留下的,祖父用過,他去上海打工,在碼頭上裝貨卸貨,用的也是它。船與碼頭之間,搭著一尺寬的跳板,挑著擔子走在上面,沒經驗的,腿會發(fā)抖,一不小心,就會栽下河。經驗從哪里來?練呀。巷子里放幾條長板凳,連在一起,權當跳板,徒手走,挑著擔子走,閉了眼睛走,練腿勁,練膽量。膽量非常重要,擱在地上的跳板,誰都不怕;抬高三尺,有人發(fā)慌;抬高一丈,多數(shù)人頭暈。雜技演員能在空中走鋼絲,這都是練出來的。
1964年,我去北京念大學,上學時因直言賈禍,陷入困境。我惶惑,寫信給父親,說不想念書了,干脆回家種田。父親回信:“人都有七災八難,捆起來經住打,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,挺一挺就過去了。大丈夫要能伸能屈,一根扁擔能睡三個人,天無絕人之路。”
“一根扁擔能睡三個人”,這句話給了我力量。我后來遇到過更大的苦境、逆境,也都是憑了這種信念,咬牙度過。
晚歲攬鏡,發(fā)現(xiàn)我和父親竟然有幾分相像,而且是愈老愈掛相。當初為什么覺得不像呢?這是因為,那時我面對的是父親的不惑之年或天命之秋,以我之稚嫩,去比照歲月的滄桑,當然是合不上轍的。如今我已邁入耄耋,五官逐漸向父親趨同,總歸是基因相承,血濃于水,繁華落盡,露了本色。
偶爾玄想,歲月是一根長長的扁擔,父親在那頭,我在這頭。
《光明日報》( 2023年05月05日?15版)
標簽: